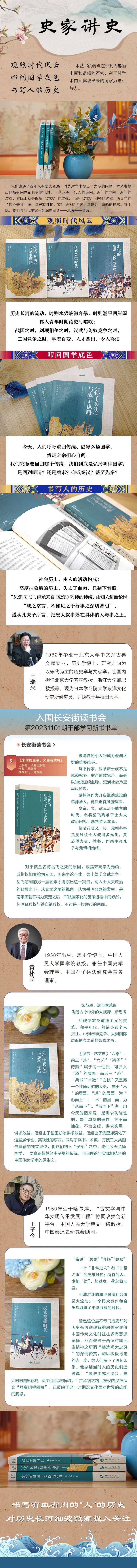导读:近日,美国“淫魔富商”爱泼斯坦案件有关联的人物身份被披露,众多耳熟能详的西方社会权贵名流深陷漩涡,世界舆论一片哗然。太阳底下无新鲜事!我们对此感到异常惊讶和出离愤怒的同时,在这巨大丑闻曝光千年前,为我们今人津津乐道的宋代文治背后的士大夫生活日常几无二致。

风流韵事,最能牵动人的兴奋神经,令人津津乐道,成为街头巷尾的传闻,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由于风流韵事多隐蔽于重重帘帷之后,所以颇能激发人之本性所具有的窥秘心理。窥秘不得,也能生出无穷想象。
此种现象,自古而然。除非严格到了男女授受不亲,否则,虽圣人亦不免艳闻上身。君不见子见南子,也弄得说不清道不明,害得孔夫子气急败坏,直发毒誓,连连说:“予所否者,天厌之!天厌之!”意即我去见那个名声不好的风流女人并没有什么不良意图,如果不是这样,天诛我,雷劈我。
圣人以降,则更是不可胜数。比如宋代的文豪欧阳修、苏轼都有艳闻,就连道学集大成之朱熹也难免。范仲淹痛感五代以来世风浇薄、气节沦丧,遂担当起道德重建的重任,疾呼振作士风。范仲淹的作为,对后来的道学起到了奠基的作用。朱熹曾这样评价他:“本朝忠义之风,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也。”所以朱熹将范仲淹视为“天地间气, 第一流人物”。在把握了主流话语权的士大夫们大张旗鼓地揄扬与塑造之下,死后的范仲淹终于上升为完美无缺的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圣人。居然,这样一位“名节无疵”的完人也有风流韵事?

范仲淹“吴东治水”
起因:一首诗惹的祸
景祐三年(1036)五月,范仲淹在权知开封府的任上,因政见与宰相吕夷简发生激烈冲突,被贬放到外地,成为饶州知州。不过,范仲淹担任饶州知州的时间并不长,实足在任仅十八个月,景祐五年一月,便改知润州。离任之后,范仲淹写下一首题为《怀庆朔堂》的绝句:
庆朔堂前花自栽,
便移官去未曾开。
年年忆着成离恨,
只托清风管勾来。
就是这短短的四句二十八个字,让范仲淹成了艳闻的当事者。本事、传闻、考证、想象,在宋人笔记、类书中津津乐道并辗转引述的范仲淹韵事,都是由这四句诗生发出来的。
在道学一统天下的明代,道学的实际奠基者之一范仲淹的精神地位极为崇高。倘若范仲淹这样的风流韵事被认可为事实,那么对于主张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的道学家们来说,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精神打击。因此,这样的事实必须否定,必须维护范仲淹“名节无疵”的道德形象。
南宋晚出的《吹剑录外集》,在叙述事实之后,还有一段俞文豹的议论:
王衍曰:“情之所钟,正在我辈。”以范公而不能免。
慧远曰:“顺境如磁石,遇针不觉合为一处。”无情之物尚尔,况我终日在情里做活计邪?张衡作《定情赋》,蔡邕作《静情赋》,渊明作《闲情赋》,盖尤物能移人,情荡则难反,故防闲之。“以范公而不能免”,无疑是认定范仲淹实有这段艳情。

求证:宋人日常
前引陶尔夫先生所云“与宋代其他士大夫一样,出入歌楼妓馆,偎红倚翠,也是范仲淹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方面”,绝非主观臆测,述说的是确曾存在的事实,这是唐五代以来的文人风习,与道德形象无关。
至少从唐代开始,官伎隶属于乐部,所以称作在乐籍,身份不自由。各地官府每有宴会,多以官伎作陪,歌舞佐兴。由于研习歌舞词曲、琴棋书画,其中也涌现出不少色艺俱佳的才女,为士大夫所倾心,许多风流韵事也因此产生。
宋人曾慥《类说》卷二九记载了一件唐代的逸事:“杜牧佐沈传师在江西,张好好十三,始以善歌来入乐籍中。公移镇宣城,好好复宣城籍中。后二岁,为沈述师着作双鬟纳之。”这个张好好年仅十三,也与宋人记载范仲淹所眷顾的幼伎年龄相仿佛。
以罢政担任西京留守的钱惟演为中心,当时洛阳聚集了一批文人。除了梅尧臣、尹洙、谢绛之外,后来与范仲淹一样,成为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也以河南推官的身份参与其中,诗文酬唱, 俨然一时盛事。是时,二十五岁的欧阳修刚刚迎娶恩师胥偃十五岁的女儿不久,正处于燕尔新婚之际。就是这样的时候, 欧阳修居然还跟一歌妓保持着亲密的关系,并且毫不避嫌,公开在交际场所出双入对。

尽管梅尧臣、尹洙、谢绛等人认为欧阳修“有才无行”,略致微辞,但作为长官并且跟欧阳修妻子有着亲戚关系的钱惟演,竟对欧阳修的行为不加阻止。因歌妓丢失金钗而宴会双双来迟,欧阳修临场赋词后,不仅得到谅解,还被加以激赏,甚至钱惟演还动用公款为那个歌妓补偿了金钗。欧阳修的行为,钱惟演的态度,都表明与歌妓等风尘女子交往是当时司空见惯的士大夫风尚。
欧阳修与范仲淹不仅是同时代人,而且两人交往密切,有过诗文酬唱。范仲淹曾举荐过欧阳修,欧阳修在范仲淹被贬官之际曾仗义执言。在范仲淹去世后,欧阳修还应范家之请为范仲淹写了神道碑。虽说行为因人而异,然朱墨相近,风尚所及,自有互相影响。
士大夫利用权力地位可以动用乐籍女子享乐,普通士人流连于花街柳巷也是当时的一道风景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柳永, 他“倚红偎翠”,为青楼歌馆女子填词写作,写下了“杨柳岸,晓风残月”的《雨霖铃》,令千古吟唱;写下了“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”的《望海潮》,让完颜亮生出“立马吴山第一峰”的南下野心。柳永为此耽误了功名,科举落第后,他写了首《鹤冲天》词发牢骚,高傲地宣称自己“才子词人,自是白衣卿相”,并说:“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。”《鹤冲天》词广播朝野,以致当他再度应试,快放榜之时,宋仁宗发现了柳永的名字,讥讽道:“且去浅斟低唱,何要浮名?”将其黜落。后来柳永穷困潦倒,一群歌伎知己为其送葬。

聚焦:日常范仲淹
柳永,与范仲淹同时代,他年过五十获得进士功名之时, 也就是在范仲淹写下《怀庆朔堂》一诗两年之前的景祐元年(1034)。
柳永这首广播朝野的《鹤冲天》,无疑也影响到了范仲淹。证据便是,范仲淹在一首词中居然原封不动地使用了“忍把浮名”四个字。我们来看一下收录于宋人龚明之《中吴纪闻》卷五的这首词:
昨夜因看《蜀志》,笑曹操、孙权、刘备,用尽机关,徒劳心力,只得三分天地。屈指细寻思,争如共刘伶一醉?人
世都无百岁,少痴騃,老成尪悴,只有中间,些子年少,忍把浮名牵系。一品与千金,问白发如何回避?
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柳永词:
黄金榜上,偶失龙头望。明代暂遗贤,如何向?未遂风云便,争不恣狂荡。何须论得丧,才子词人,自是白衣卿相。
烟花巷陌,依约丹青屏障。幸有意中人,堪寻访。且恁偎红倚翠,风流事,平生畅。青春都一饷,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。
上述范仲淹的词,与被宋仁宗揶揄的柳永词,何其相似乃尔!

"白衣卿相"柳永
人生不满百,好时更无多。草木一秋,流水一程,无论高贵,还是富有,都留不住一天天逝去的生命。“尔曹身与名俱灭”,政治是灰色的,浮名为过眼烟云。把有限的宝贵生命, 牵系于浮名,直如少不更事的痴騃,真不如与刘伶为伍,珍惜生命,把握青春,陶醉于酒中天地。人都是多面体。有这样的人生观,有这样对生命的彻悟,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与士人习尚下生活的范仲淹,既是生命的自觉,又是流风所及,自然不会脱凡超俗。
紧接在《怀庆朔堂》之后,范集有《依韵酬叶道卿中秋对月二首》,诗中的“处处楼台竞歌宴”,正是对士大夫歌舞升平场景的形象写照。
范仲淹后来知邓州时所作的一首《中元夜百花洲作》诗中,也描写了他宴游歌舞的场面:“客醉起舞逐我歌,弗舞弗歌如老何?”人生苦短,及时行乐,时不我待,这也是再普通不过的人之常情。在邓州,范仲淹写的《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酝》中,有这样的诗句:“长使下情达,穷民奚不伸?此外更何事,优游款嘉宾。时得一笑会,恨无千日醇。”范仲淹的宴游, 是在政事之余,所以与他的政治理念并无相违。
宴会歌舞,是宋代士大夫的日常生活。正如范仲淹在《依韵和同年朱兵部王宾客交赠之什》诗中所描述的那样:“西园冠盖时时会,北海樽罍日日亲。”杯觥交错,弦歌轻舞。微醺之中,范仲淹从异化的官身返璞归真。他在这首诗中还如此写道:“共弃荣华抛世态,同归清静复天真。”

通过俯瞰宋代士大夫的时代风尚,像唐代的文人杜牧喜欢年少的张好好一样,范仲淹喜欢一个女子毫不奇怪,并非不可理解。不过,我猜想范仲淹喜欢这个歌伎,更多是喜欢她的天真烂漫,而非肉欲。
出世与入世,一直是传统士大夫精神世界相反相成的两面。得意之时奋进,失意之时放纵,亦时有之。屡屡遭受政治打击、贬放外任的范仲淹,诗中多次出现“吏隐”这个词, 表明他神往林泉之意。当此之时,范仲淹需要的是另一种麻醉或者说是精神慰藉。吟诵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,同样也吟诵过“自古荣华浑一梦,即时欢笑敌千金”。
对纳入乐籍视同贱民的女性,范仲淹也充满同情与怜爱。宋人吕本中《童蒙训》卷下记载了一件事:
范文正公爱养士类,无所不至。然有乱法败众者,亦未尝假借。尝帅陕西日,有士子怒一厅妓,以瓷瓦劙其面, 涅之以墨。妓诉之官。公即追士子,致之法,杖之曰:“尔既坏人一生,却当坏尔一生也。”人无不服公处事之当。
官伎多是贫家女生计无着卖身入籍,地位几同奴隶,所以有些无良士人不拿官伎当人看。这条史料记载的士人迁怒于一个官伎,竟然用瓷片划破官伎的脸,还像刺青一样涂上颜色,跟朝廷防止士兵逃跑所用的对待士兵的方式一样。这样残虐的做法,不仅仅是羞辱,等于是毁容,让主要靠容颜为生的这个女性没有了活路。这个官伎告到范仲淹那里,范仲淹异常震怒,说既然你毁了别人的一生,一报还一报,你也要搭上一生。他严厉地处罚了这个无良士人,为那个无辜的女性出了口恶气。从对残害官伎士人的严厉处置,可以概见范仲淹对女性的同情与尊重。

在传统中国,多数女性深处内闱,“养在深闺人未知”。男人奔走于外面的世界,政治、权术、利益……一切都是昏暗的拼杀、博弈,于是,舞榭歌台、浅斟低唱便成为一道亮色,让他们紧张的神经得以松弛片刻。客观的需要就有了客观的存在。范仲淹,也是常人。
然而,历史上的正面人物,在其死后,却大多被锦上添花,涂脂抹粉,包裹上厚厚的油彩,塑造成道德的标本。这样的标本无血无肉,无情无欲,活像一具具让人难以亲近的木乃伊。这绝对不是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。
王衍说的好,“情之所钟,正在我辈”。为亲者讳,为尊者惜,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。历史研究,不是强化道德说教。对于已经风化得只剩下骨骼的历史人物,需要怀着一份温情,本着科学精神,缜密考证,找回那一个个鲜活的灵魂,还原曾经丰满的血肉。“情之所钟,正在我辈”,这也是历史学者的使命。(文章摘自 王瑞来《宋代的皇帝、文臣与武将》)